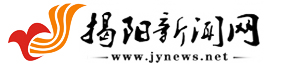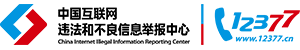在近代史上,榕城有个榕江书院(即现在揭阳一中南校区),有关它的图文,在县志中占了很大篇幅。所以,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榕城作为揭阳县治,什么时候开始建设书院,先后建了多少书院,却就未必众所周知。
笔者对于这一地方文化现象,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凭借文献而知,榕城的书院,应以明末的文起书院为发轫。继之而有清代康熙时期所建的龙起书院,乾隆时期所建的榕城书院、近圣书院和榕江书院。影响较大者,是榕城书院和榕江书院。
乾隆揭阳县志卷二《祠坛》“韩昌黎祠”条,末有文云:“后为文起书院,崇祯二年知县冯元飚建,并置蓝都山浦尾田四十九亩,租谷九十九石二斗零。每年除祭祀及完粮与守祠人灯油饭食外,余为诸生科举卷资。”这座文起书院于清朝前期被改为“冯侯祠”。乾隆县志“冯侯祠”条记载了这一变迁:“在韩祠后,即文起书院。绅士改建以祀明知县冯元飚。”文起书院的出现,可谓昙花一现,而由之改建的“冯侯祠”,至建国后也被改为公用建筑,现在是某一银行的分支机构。
康熙初年所建的书院,还有雷神庙后的“龙起书院”。它是康熙初年揭阳知县,后升迁为水部主事的绍兴人胡鹤翥捐建,所以书院兼祀胡公神位。至乾隆后期,儒风萎靡,书院遂被改为“禅院”以供佛,旁祀知县胡鹤翥不变。如同文起书院,这一书院在揭阳也是稍纵即逝,很快消亡。
榕城的又一书院,史失其名。它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阖邑士民建为知县孙公瑜生祠,(孙)辞不受,以揭为朱子经游地,又与其祖烛湖先生为友,令并祀”的产物。就是说,它是孙公瑜把揭阳士民为其所建的“孙侯祠”改建,书院作为教学场所,同时兼祀朱文公与孙烛湖两位先贤。同时,孙公瑜还“捐置渔湖白宫、枋桥田一十八亩,租谷四十三石四斗五升为馆师修脯”。至乾隆末年编修县志时,这处书院已“归榕城(书院)掌教、收管。”当时,绅士又合置田地以供养。显而易见,这座未名书院后来成为榕城书院的一部分。县志于卷二《学校》一目中为其置“书院”一名,标明“在韩祠右”,即今韩祠路新生电影院老址对面。
康乾年间创建于上述书院左近的榕城书院,是榕江书院问世之前榕城最大的书院。县志《学校》一目中专为记载其“官荒田地租”数额,自乾隆十五年(1750)知县顾彝开始拨置,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刘业勤拨置,先后有多任知县拨入地产19宗,约1000亩并有相当数额的其他地租、铺租,其规模相当庞大。此外,还附设有武书院,揭阳乾隆之后的不少武举人、武进人,都是该院培养。在县志中,记录了知县刘业勤两次向武书院拨入“膏火”的数额。基本上都是衙前铺屋的铺租,每次都只有一十千文左右的数额,数额不算很大,也反映当时习武的学生不是很多。
在揭阳学宫的文昌阁后,还有乾隆十六年(1751)知县顾彝倡建的近圣书院。玉浦进士黄世杰、在城进士许登庸等地方知名人士都曾掌教于此。然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为学宫部分建筑年久失修而倒塌,存在20余年的近圣书院(今训导署)被“暂借为住宅”,从此“一去不复返”,以至后人根据光绪县志舆图所示而把它认定为“训导署”。
至于榕江书院,则是乾隆八年(1743)揭阳知县张薰买贡生许之翰的别墅地六亩九分及房屋18间为基础创建,并逐步扩大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榕江书院的前身和基础。在创建、扩建过程中,知县张薰、顾彝、王壂、刘业勤,诸生许之翰等均有捐助,为揭阳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兵荒马乱,一时为粤东学校翘楚的榕江书院,竟然没有培养出几名有影响的科举人才,倒是进入民国,教育“转型”之后,才成了人才辈出的渊薮。
榕江书院建成于乾隆后期,有“八景”之美,刘业勤等揭阳内外人士也分别即景赋诗,使之文采风流,蔚为大观,为揭阳的书院历史,画上完美的句号。
可惜榕城所有的书院,已经全部“随风而去”,能够留存的,只是零星的文献以及美丽的传说。
(编辑:袁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