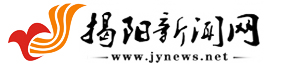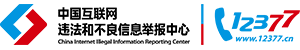10月下旬,时值深秋,我来到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的老君山,来到这座传说中老子归隐修炼成仙的道源地。
在十里画屏目睹壮观的云海后,夜晚在狂风、浓雾、低温中蜷缩入睡。第二天,我照例早起看日出,狂风与云雾搅得天地混沌,身心跟着云海沉浮。大约上午8点半,风停,世界仿佛也静默了,耳边只剩下雾凇在凝结或融化的轻微声响。
山顶上,道德府巍峨居中,五母金殿、亮宝台、玉皇顶呈“品”字铺开,熠熠生辉,而托举道观的山体轮廓如鸾鸟展翅,微微昂头,披着银白的羽毛,款款而来,殿顶在素白世界里,静静悬浮。
亮宝台与玉皇顶持续散发着朦胧水汽。通往两座宝殿的山路近乎垂直,两边的松枝裹着雾凇,松针尖上挂着的细小白粒被风一吹,颗粒落在衣领上,凉得像碎冰;蹭到指尖时,有砂纸般的细涩感,走不了多远,衣领上就积了一层薄薄的“霜”,拍一下,悉悉落在石阶上,声音轻得仿佛蚕吃桑叶。
站在玉皇顶,在顺逆光的交织区,山脊线由暖橘到冷灰,由远及近一层层被勾勒出轮廓,天地间化作一张巨大的画布,雾凇显影,每一根松针都成了画的笔触。宝殿铃铛声犹如冰晶碎裂声,既清脆,又冷峻,震颤着心尖,只得屏住呼吸,轻迈脚步,生怕大声说话,震落更多雾凇,但鼻腔里仍沁入丝丝松针与冷空气混合的清冽气息,这是老君山雾、松、风与阳光交汇的独有味道。
如果说雾凇只是金顶道观群的配角,那在马鬃岭,雾凇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马鬃岭为800里伏牛山主峰,最高峰海拔2217米,前峰如马头,后峰似马背,马背上的草木宛若马鬃,而两峰之间的绝壁长廊恰似一条腰带,将两座雾凇仙山连在一起。侧看,两座山峰又好像两片凌厉的刀片,将老君山切成两个世界,阳面以花岗岩为主,阳光下坡面青灰,树木红绿,阴面的华山松则“千树万树梨花开”,雾凇如同无数宝石铺满整面山坡。
更神奇的是,山脊线上的松树,山阳恒温枝桠仍葱郁舒展,山阴低温枝叶则晶莹雪白;上部皎洁得如怒放的花儿,下部却青翠得要滴出水来;迎风处雾凇细密挂满松针,背风处枝叶却仍欲挂还羞;秋日的绚烂多彩与寒冬的冰肌玉骨罕见交融了。
一夜狂风的风向和风量,被凝结成长短胖瘦的雾凇。蹲下身,指尖轻碰松针上的雾凇,细涩的颗粒粘在指腹,凉意在掌心蔓延;再次触碰,颗粒顺着指缝滑落至石阶,碎成更小的白点,不见了。
登上山巅无为亭,蓝天下红黄绿相间的叶子、清澈的雾凇、金光闪闪的宝殿,描绘出一派天上风光。长耳鸟“呜呜呼”在雾凇林间环绕,振翅腾飞时,雾凇颗粒簌簌而下,而后又重返松林。
正前方的宝殿四周被雾凇锁住,山脚是栾川县城,雾中县城,时隐时现,天宫与凡间同框了。身处山顶仙境,四周却皆为喧嚣的凡人,而高楼林立的县城,却在朦胧中一片安宁,究竟哪里是仙界,哪里是人间,或仙界与人间本无界限?
老君山见缝生长的迎客松,始终自然弯腰迎接游人。腾云栈道上的行人细如蝼蚁,来去匆匆,而雾凇虽凝结又消融,却年年复见2500年前的壮美。当年老子隐居时,究竟是走进雾里,还是走进仙境?不得而知,但自己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边走边拍时,宛如凌波微步,似乎双手张开就能飘起来。
游至近午,阳光渐烈,雾凇融化加速,松针上的白色颗粒顺着叶脉滑落到地上,汇成一滩细小的水洼,映射着宝殿的金光。站在树下,看着一片雾凇从完整到消散,不过半盏茶工夫,剔透的枝叶只剩下湿漉漉的墨绿。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恒常的圆满,原来“顷刻的繁华”才更让人珍惜,好比这趟旅程,本无期盼,却因这“顷刻”的雾凇,回家后仍常翻相片。
感受“秋雾凇”时,总想起《道德经》。山脊线上的松树最懂“无为”,阳面的枝桠不刻意向阳伸,只是顺着暖意伸展,叶尖仍带秋日的浅黄;阴面的枝桠不抗拒低温,每根松针都裹着雾凇,像捧着一团细碎的月光。它们不与温争、不与风斗,阳则绿、阴则白,却在“顺应”中长成老君山最挺拔的姿态。原来“无为”从不是“不作为”,而是如松针裹雾凇一样,接纳风霜雨雪,却不失本真。
从清晨6点半徒步到下午4点半,从山巅游览到山脚,连早午餐都忘记吃,却没明显的饿感和累感,身体仿佛成为松风与彩林的一部分,与融化的雾凇同呼吸,在变幻莫测的光影中找到通灵感。
回到山脚时,再想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突然懂了:老君山的雾凇,从不是奇观,只是山、水、风、温、光顺应规律的结果;赏雾凇者,亦非旁观者,而是在凝结与融化中触摸“道”的温度与厚度。也许“道法自然”,从不是远在经书里的道理,而是近在雾凇沾衣的当下,与松风拂面共振的瞬间。
谢锐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