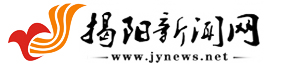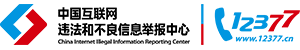春分已过,窗台那盆海棠依然沉默。褐色的枝丫像被岁月风干的血管,在晨光中固执地保持着冬日的姿态。我日日浇水时总要与它絮语:“该醒了”,它却只是抖落几片去年残留的枯叶作回应,仿佛蜷缩在时光褶皱里的老者,对春光视若无睹。
直到某个雾霭迷蒙的清晨,一抹翡翠色突然刺破铁锈般的枝干。指甲盖大小的新芽蜷成婴儿的拳头,绒毛上还凝着隔夜的水珠。我握着喷壶的手微微发抖,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虹光——原来它不是在沉睡,而是在泥土深处编织着春天的密码。
教室后排靠窗的少年总把自己种在阴影里。
校服领子永远竖着,像是竖起无形的盾牌。物理课讲到多普勒效应时,他的课本下压着张皱巴巴的速写:扭曲的钟楼尖顶刺穿云层,齿轮状的月亮咬住半片星空。铅笔印被反复描摹得近乎晕染,像某种隐秘的求救信号。有次收作业时,瞥见他草稿本边角画着机械鸟,翅膀关节处精密如瑞士手表,羽毛却是梵高《星月夜》的笔触。
三月细雨浸润窗棂的午后,他的堡垒出现了裂缝。
阳光斜切进教室时,少年突然摘下卫衣帽子。他侧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睫毛在眼睑投下齿轮形状的阴影,手指跟着雨滴滑落的轨迹,在雾气朦胧的窗面画下螺旋线。那些银亮的纹路在暮色中舒展,竟与海棠枝头初现的花苞惊人相似——都带着某种笨拙而执拗的弧度。
此后每个清晨都藏着礼物。嫩叶舒展成碧玉雕琢的团扇,花苞像少女发髻上的珍珠簪子,直到某个黄昏,整株海棠突然燃起漫天红云。那些绯红的花瓣重重叠叠,仿佛千万只蝴蝶正振翅欲飞,连晚风经过时都放轻了脚步。暮色里,我分明听见生命拔节的脆响,看见沉默的根须如何穿越黑暗,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一寸寸丈量春天。
少年课桌上的堡垒日渐低矮。
某天晨读时,发现他破天荒地没戴耳机。摊开的《三体》扉页上,铅笔勾勒的太空电梯从书脊直通天际,电梯轿厢的舷窗里透出点点荧光——细看竟是缩小版的海棠花。当我把自制《科幻世界编年史》轻轻推到他面前时,他耳尖泛起海棠初蕾般的淡粉,手指却将书角捏出细密的折痕,仿佛握住了一颗正在解冻的星球。
就像去年总在实验课上打翻量杯的女生,今春竟能用试管调出渐变色的虹;总把英语单词写成五线谱的男孩,如今在合唱团领唱时,连窗外爬山虎都在和声。原来那些被我们误读的“错误”,不过是生命在调试绽放的波长。
泥土里埋着无数未校准的时钟。有些种子要等惊雷劈开硬壳,有些根茎需寒潮唤醒甜蜜,就像高山杜鹃总要积攒三年光阴才肯吐露芬芳。当我们焦虑地丈量幼苗的高度时,或许地底的银白根系早已悄然织就星图。
此刻海棠依旧在晚风里摇曳,褪色的花瓣正轻轻叩击窗棂。那些飘落的花盏多像时间的邮戳,提醒我们在所有看不见的成长里,都藏着生命庄严的叙事诗。而我要做的,不过是把每个少年的沉默翻译成季风,等待他们自己选定破茧的坐标系。
(作者系普宁市流沙第一实验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