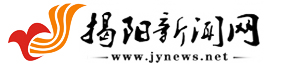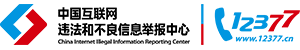●“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207)

赐书楼鸟瞰。郑楚藩 摄

赐书楼位置图。阿 龙 制图

20世纪80年代的赐书楼门楼。陈作宏 提供

院落里民居门牌上写着“东门花园内”几个字。池 妍 摄

陈作宏(右)在赐书楼院子里讲述当年丁日昌、王韬讨论军国事历史。阿 龙 摄

陈作宏(右)在引榕干渠边说,当年丁日昌乘船至此上岸,来到赐书楼。阿 龙 摄

赐书楼后墙。郑楚藩 摄

赐书楼已成危楼。郑楚藩 摄
在榕城区望江北路东升街口西南侧,有一座占地1亩多、三进式、坐北朝南的破旧老院落,院落里的民居门牌上写着“东门花园内”几个字。很多人不知道这座残破不堪的建筑,曾是揭阳榕城一处显赫的私家园林,它的原来主人是晚清著名政治活动家、洋务运动实干家丁日昌于清同治年间营建的絜园赐书楼。
2024年冬,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走近这座历经近150年风雨的赐书楼,寻觅这处文化遗存的沧桑变故。
絜园系丁日昌私家园林
花园内地名,源自丁日昌私家园林絜(jié,揭阳音giag4 (洁),古同“潔”,1955年作为潔的异体字停用,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括注姓氏人名除外)园。据2024年《环城榕色》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丁忧在籍,因“乐揭邑岩泉之秀丽”,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揭阳东门外“村郭间购得一废圃,葺茅茨,辇树石”,建成絜园,俗称丁家花园。
絜园之名是沿袭丁日昌在上海道署所建园林的名字,取“洁白戒养之意”,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园定名题匾,并作《絜园记》,成为有名的法帖,流传至今。絜园襟紫陌而依榕江,带水负郭,地僻景幽,古槐接天,苍松蔽日,怪石奇花,为揭阳当地名园。园中的建筑物有赐书楼、五间楼、三间屋、待月亭、水亭、草堂、东山亭、半园、曾公祠(祀曾国藩)等,可见絜园的建筑规模。
建成后的絜园,成为接待远近来揭官员、学者的重要场所,而赐书楼则是宾客下榻之处。据文献记载,丁日昌晚年在揭阳养疴期间,先后来揭拜访他者,有晚清洋务运动思想家、政论家王韬,咸丰九年探花、同治朝侍读学士李文田,江南道御史钟德祥,天津道柯欣荣以及邻近各级官员和文人墨客等。光绪五年(1879),王韬专程拜会丁日昌,下榻于赐书楼计六七日,与丁氏朝夕相处,探讨洋务及其他军国大事,论及台湾及琉球问题,在“整顿海防、制造军舰、训练水师”等方面形成共识,认为“决不可缓”。这次会见,成了洋务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丁日昌与王韬曾在此讨论军国大事
揭阳市文史专家、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揭阳市文化局局长的陈作宏在其专著《沧桑百多载,何处诉风流?》中述及了丁日昌在絜园与王韬讨论军国大事——早在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王韬通过黄达权,在广州认识了丁日昌。两人有过一次长谈,在“师夷制夷”,办洋务富国强兵方面理念一致,主张相同,故一拍即合,惺惺相惜,从此时有书信往来,相互讨论洋务及海防军国大事。王韬赞丁氏为“一代伟人”。丁氏赏识王氏,认为“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没人能与其相比,多次将其“揄扬”给“南北诸大僚”。王韬于是视丁氏为“生平第一知己”,“极思感激驰驱以报”。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一中,有一封他抵揭拜会丁氏离开后给丁氏的重要信件。信中说他在絜园逗留了六七日,园中“花木纷绮,泉水溁洄,临流对山,殊有远致,一切布置,非胸有丘壑者不能”,令他“叹为观止”。其时“连日下榻园中者凡三十八座,可称一时盛事”,每用餐王氏“必居首位”,故亟赞丁氏“爱才下士,往古所无”。在此,他饱览了丁氏所藏“奇编秘籍”,惊奇为“海内所罕”。他“日侍”丁氏“左右”(可证他与丁氏一起均下榻于赐书楼),亲见丁氏“凌晨而兴(起床),深夜不睡,书牘往来,宾客谒见,无有暇晷(空闲时间),每食不过一盂。每遇事故,则裂眦扼腕,叹息累日”;办事如“雷霆无比精锐”,虑事则“毫发无此精详”,终日“殚心瘁力,罔自爱惜”;“每遇一事,不独以精神注之,直欲以生命赴之,此古今所未有”。
此信更论及台湾、琉球问题,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为患日深”,“整顿海防,制造军舰,训练水师,决不可缓”。对朝廷欲加丁氏总督衔、经略沿海七省水师,丁氏以病力辞,他认为丁氏“能任大事,能肩巨艰”,“能为人之所不能”,劝丁氏“为朝廷计,苍生计”,“断不可不出”。可见,留絜园期间,两人讨论的均是军国大事,信中这些述说,系他再次向丁氏提出的剖心建言。临别,丁氏赠王“异书”馈以金帛,还“函呈总理衙门”,并修书向沈葆桢和何瓂两位总督推荐王韬。
陈作宏老师认为,这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见,为絜园及其赐书楼添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闪光芒。遗憾的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甲午战争惨败,赔款割让台湾。历史的悲剧,终于被这两位爱国志士当年不幸言中,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彻底推行并挽救中国命运,也让絜园及其赐书楼染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赐书楼”因珍藏清廷御赐书籍而命名
赐书楼是絜园附属的一座建筑,也是整个絜园建筑硕果仅存的一座。
赐书楼坐北朝南,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院落第一进为大门,门两侧有库房。二进为三开间一厅二房。三进系倒“凹”字型七开间六房一厅,双层灰墙木楼后包,形制类丁日昌兴建的百兰山馆。前后有两天井,前天井两厢有盖顶亭屋相向,中间从两根石残柱看,似有一座亭式建筑。院落东西靠墙有盖顶通栏贯穿前后三进建筑物。整座院落建筑物层高比普通民房高出一筹,糅合了苏杭园林建筑和潮汕传统建筑风格。
那么,这座院落为何命名为赐书楼呢?据陈作宏老师考证,光绪二年(1876)的二月和六月,皇帝先后赐给王公大臣、内廷翰林和各省总督、巡抚两部书,一部叫做《平定粤匪方略》,一部是《平定捻匪方略》。后来,光绪皇帝又赐给一本《同治皇帝诗文集》。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将这三部书储藏于这座院落的楼上,并将这座院落命名为“赐书楼”。
赐书楼系絜园仅有遗存
丁日昌夏季喜园居,晚年病退揭阳养疴,夏天必居絜园并下榻于赐书楼。《百兰山馆古今体诗》卷五有关诗篇,有“一屋安笔砚,一楼置书史”之句;有“太守”“刺史”“司马”“明府”“广文”(负责教育的官吏)等粤东地方府、县官员经常前来拜谒请安,文人墨客友人来访相互唱和,以及“絜园文课,至者三百余人”等有关文字。可见赐书楼这座院落,是丁日昌晚年除百兰山馆外另一藏书、起居、养病、休憩、读书、处理公私文牍、接待宾客、设坛延师课徒的重要场所。当年,丁日昌在这里写下了不少重要文章、诗词和对联,这位晚年“奉准在籍专折奏事”(李文田《丁公行状》)的封疆大吏,在揭阳期间给朝廷多件涉军国大事的建言奏折,部分就在这里写成。
可惜天不假年,光绪八年(1882),一代名臣丁日昌病逝于榕城,因找不到合适的墓地只得暂处絜园,后埋于园中,后人称“丁中丞水冢”。丁日昌逝世后,家族日渐中落,一度官宦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的絜园盛况已然风光不再,但仍有士夫阶层不时来此凭吊怀旧。台湾晚清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著名作家许地山之父)、大埔举人邓尔紮等,就曾到此凭吊流连缅怀赋诗。
民国时期,絜园的部分用地曾先后被出租,用作养鸡公司以及木材店等。20世纪50年代初,絜园中丁日昌墓葬被盗掘(后移葬于榕城仙桥紫陌山)。1957年,絜园被改建成揭阳县华侨中学,赐书楼也被丁氏后人变卖。
亟盼赐书楼能得到保护、修缮
冬日里,采访组在陈作宏老师带领下来到东升街中段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从巷口拐进几个弯,穿过逼仄的小巷,可以看到一座高大气派的石门框,门上楷书的灰塑门额“赐书楼”三个大字至今犹存。两旁落款被涂上白灰,但依稀可认出上款为“恭储光绪二年”字样,下款为“御赐方略”字样。
从大门进去,记者看到,园内房屋断垣残壁,杂草丛生,显得十分荒凉。整座花园的建筑物大部分已被拆除,基本变成民宅,但大门还剩下半扇高大的门板孤独地坚守着。历经百年沧桑,原来的辉煌已经被时光掩埋,如今的赐书楼剩下的是破败不堪的景象。
“前面的八字形麒麟照壁原来非常精美,从大门到照壁之间是宽阔的麒麟前埕。前天井还有一个八角井和一个圆井,井里的水与榕江相通。”71岁的郭潮明,东门郭氏后人,自小在这里长大,提起孩提所见院落情景时,他唏嘘不已:“原来这里住着40多户人家,如今,这座院落已成危房,原住户多外迁,现在只剩下几户人家在这里居住。”
园中现存的一座二层木楼,是当年丁日昌读书、藏书之地,楼台前面有走廊并设有木栏杆,楼上大部分木板窗仍然保留着,楼梯口被人锁住,但听说楼上还有住户。楼的东面有个小门,从小门出去再穿过小巷可以通往望江北路。“以前赐书楼北面的这条小溪是东护城河,直通榕江。当年丁日昌就是乘坐小船到这里上岸的。”陈作宏老师指着赐书楼北侧如今已化身为引榕干渠渠段的小溪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已是耄耋之年的陈作宏老师始终心系文化事业,为保护文物遗产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认为,丁日昌和王韬,均系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这座赐书楼,与这两位著名人物有关,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近代史教育意义的重要史迹和具有特色的近代建筑,加之全国现存之历代“赐书楼”建筑并不多,其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自不待言。虽然现在局部建筑被改建,但总体结构基本完整,亟盼赐书楼能得到保护、修缮并得以合理利用和管理。